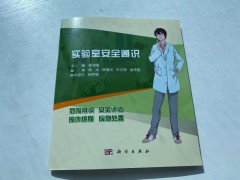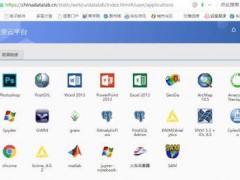當ChatGPT問世后,前沿科技帶來的沖擊波,讓我們感受更加深刻。
為何它誕生在美國,是偶然,還是必然?美國的創新生態系統有哪些特色?
2022年,美國生物科技公司Vaxess Technologies的聯合創始人——利維奧·瓦倫蒂發布的一篇行業報告:深度科技創業——從實驗室到影響力,帶給了人們許多啟發。
如感興趣,后臺可回復 “報告” 二字提取相關文件。
齊珂帆 | 撰文
葉水送 | 責編
01
前沿科技:從實驗室走向社會應用
2022年,由哈佛大學貝爾弗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針對“科技和公眾利益”項目(TAPP)出版發布了一份《深度科技創業——從實驗室到影響力》(《Deep Tech Entrepreneurship: From Lab to Impact》)報告。
這份報告關注的人可能不是很多,但它很好地詮釋了如何將前沿科技轉化出來,造福社會,并闡述美國的高科技創新模式,哪些力量在助推高科技從實驗室走出來,進而成為一個前端技術,造福社會。
TAPP項目向我們展示了科技和公眾利益對于人類社會的發展都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我們不能舍此忘彼。
該項目由貝爾弗中心主任、麻省理工學院創新研究院和美國前國防部長阿什·卡特(Ash Carter)創立,旨在確保新興技術的開發和管理符合全體公眾的利益。
阿什·卡特,圖片源自Wikipedia
報告中指出,一方面,技術變革能極大地便利我們的生活并發展生產力,而另一方面,對新技術的管控也十分重要。稍不留神,便會帶來無法預見的破壞性后果。
因此,技術變革不僅是機遇,也是挑戰。
02
美國深度科技的崛起,由哪幾股力量助推
在過去五年里,創業和風險投資界發生了一些震蕩。
有些投資者十分樂意把注押在一批特別的公司上,它們有的專注于開發電動汽車,有的專門研究mRNA技術,有的聚焦于商業太空艙……
我們能夠看出,這些公司的共同點是:以研發科學技術為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風險投資者指出,下一批萬億美元規模的企業很可能誕生于這波技術革命當中。
這些科技公司,被稱為“深度科技企業”。那么,它們有什么特點呢,我們一起來看看。
深度科技,需要以科技為根基。雖然深度科技企業在研發技術的過程中,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并存在一定的技術風險。但同時,它們也具備廣闊的市場前景和可觀的商業利潤。
由此,引得許多投資者們進入深度科技公司的懷抱。
深度科技“涉足”的領域,圖片源自Deep Tech Entrepreneurship: From Lab to Impact
此外,深度科技作為一種新的創業模式,還能解決許多社會問題,促進社會可持續發展。
如社會脫碳、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醫療系統改革、能源現代化等問題,都可以成為深度科技大展身手的舞臺。
那么,深度科技發源于哪里呢?
創新力量的主要來源地,圖片源自Deep Tech Entrepreneurship: From Lab to Impact
學術領域,是深度科技的一個重要發源地。如今,美國大部分深度科技初創企業都源于學術陣地,一些大學允許并鼓勵大家在學術研究中建立初創企業。
羅伯特·蘭格是美國科技轉化方面旗幟性人物
數十年來,麻省理工學院(MIT)的蘭格實驗室(Langer Lab)等學術實驗室一直致力于將實驗室里的科學發現轉變為能夠在社會中流通和使用的技術類商品和服務。
據波士頓咨詢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的深度科研報告(Deep Tech Report),2016年約有160億美元投資到深度科技企業,而到了2020年,這一數字便已接近600億。平均投資規模也從之前的1300萬美元飆升到了4400萬。
可見,如今的深度科技領域成為了投資界“新貴”。
從投資界對深度科技企業的投入資金來看,有三大趨勢:
第一,投資者越來越看好新技術,愿意對其進行長期押注。盡管這些科技新秀企業的成長需要漫長的時間,并且投資者需要應對市場的不斷變化,但他們依舊選擇承擔風險,將資本注入其中。
第二,深度科技研發是一個分時期進行的大工程,通常需要多輪融資,這也表明投資者在技術發展的多個階段都對相應的科技初創公司有著濃厚興趣。
第三,深度科技正在成為席卷全球的一股風潮。波士頓咨詢公司的另一份報告指出,從地理上看,在2015—2018年,美國和中國在全球深度科技公司的私人投資中占到了80%。
雖然美國堪稱全球深度科技企業中的領頭羊,但近些年來隨著其它國家的崛起,它所占的份額在逐漸下降,例如中國、德國、英國和以色列是深度科技公司也在崛起,投入的資金增長在穩步增長。
03
深度科技的另一推手:國家實驗室
目前,越來越多的創業者和風險投資人士對大學實驗室進行考察,想要從那里發現新的深度技術商業點。
新型先進材料、量子計算、合成生物學、AI、算法、生物醫學……這些都是當今備受歡迎的深度技術領域。它們大多來自大學實驗室,而后被挖掘成為深度技術熱點。
但在美國的創新生態系統中,有一個被低估的小眾來源——國家實驗室。這是推進深度技術商業化的一個潛在新興參與者。
國家實驗室的重點在于,它們先天具有服務于公眾利益的屬性和意識。
例如,MIT管理的林肯實驗室(Lincoln Lab),專注于國防應用,并且有雄心通過創建附屬產品來強化自己的商業性。
林肯實驗室的副產品,圖片源自《Deep Tech Entrepreneurship: From Lab to Impact》
然而,潛力巨大的另一面是“不夠成熟”。在將新科技轉化為商業產品的道路上,國家實驗室還算初出茅廬,需要繼續探索發展模式。
然而,國家實驗室已經用實力證明,它擁有著巨大的技術優勢。2019年,美國政府報告,國家實驗室占有研發投資總額的10.5%。其中,41%的的資金用于基礎研究,36%用于應用研究,而24%用于先進原型設計與開發。
最開始,美國的第一個國家實驗室FFRDC RAND成立于二戰后,服務于冷戰所需要的科技支持。
如今,國家實驗室的研發方向已經拓展到各個領域。美國的國家實驗室可謂實力雄厚、人才濟濟——擁有150億美元的年度預算以及六萬余名科學家、工程師。
這代表了美國乃至全球最重要和最活躍的科研系統之一。
目前,美國的13個聯邦機構總共資助了42個國家實驗室,涉及的領域十分廣闊,從清潔能源、納米技術,到癌癥研究、材料科學、天文學等,應有盡有,大到影響全球的重要項目,與我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美國當前國家實驗室列表,圖片源自Deep Tech Entrepreneurship: From Lab to Impact
通常情況下,歷史上國家實驗室開發的IP產業都將授權給到了大型企業集團或傳統的國防公司,初創企業并不在它們的名單之上。
但今時不同往日。隨著社會發展,讓初創企業獲得技術研發權,能夠產生巨大的經濟效益和良好的社會影響。所以,把充滿創新力量的科學技術鎖在實驗室里,絕非明智之舉。
04
總結
在這份報告中,作者為幫助創業者發現國家實驗室正在開發的重點技術,尋找商機,提供了一些建議,這對我們也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首先,新興的科創企業需要從國家實驗室的研發項目中敏銳捕捉到具有商業前景的科研技術,并且向相應的實驗室申請授權。
其次,便是明確基礎技術在相關領域的應用。這可以幫助他們將知識產權從實驗室轉移到私人領域。
另外,充分利用政府的政策支持以及資金支持,來擴大生產規模,推進商業化進程。
同樣,深度科技公司也可以反哺社會。它們能夠促進就業,增加財政收入,解決氣候變化、醫療資源緊缺、國家安全等諸多難題,促進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總的來說,科技是社會發展的第一動力,而將新科技轉化為經濟效益和社會影響力,則是促進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